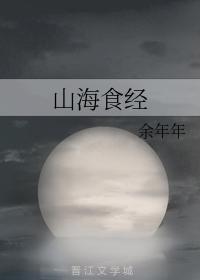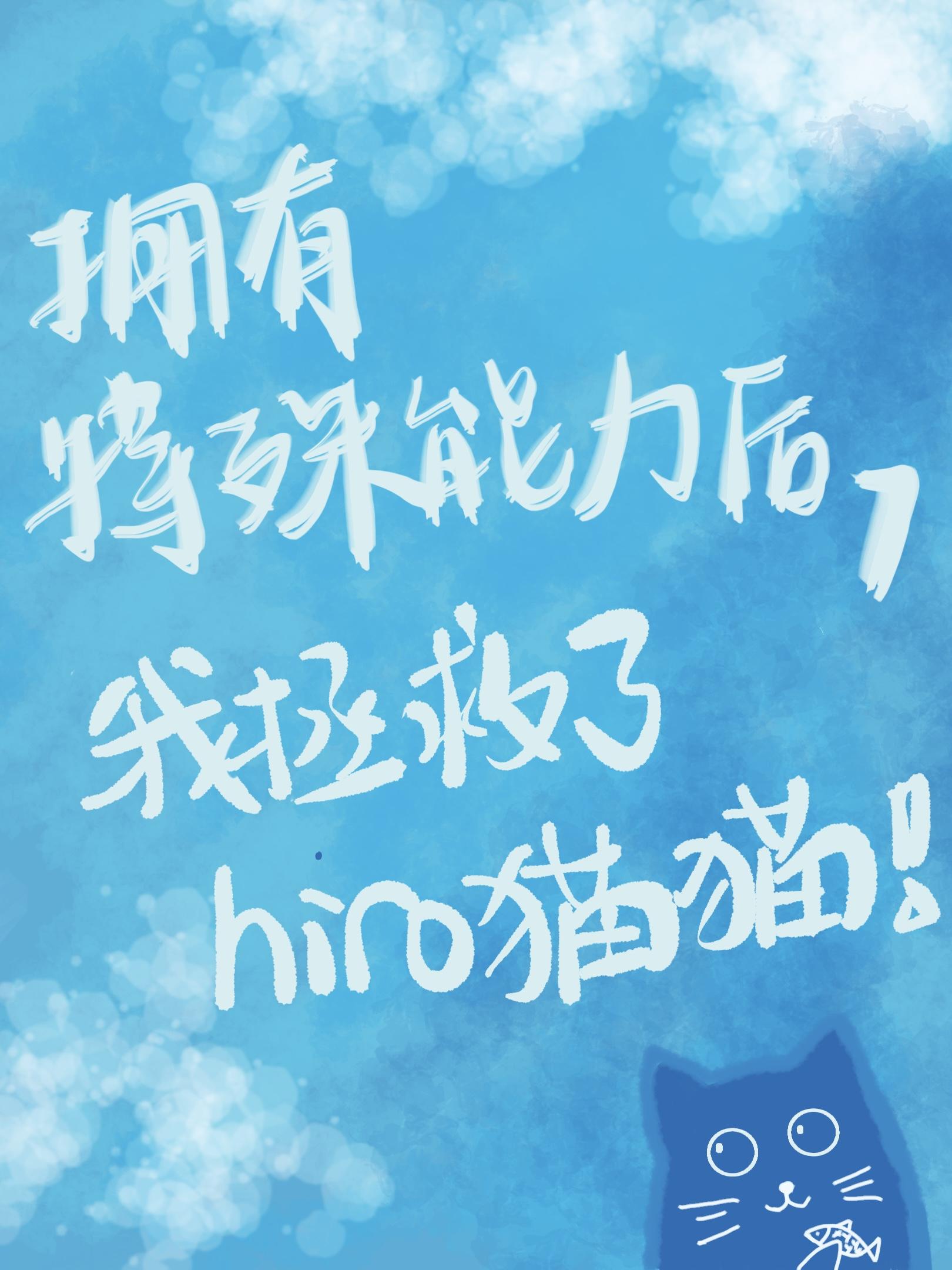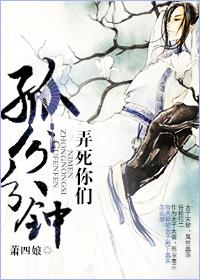遲遲等候,皇帝卻不歸來,甚至連點消息都不托人帶回來了,顧惠懿每天見到的後宮仍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模樣,所有的腥風血雨被阻絕在外,而前朝有的,又有是怎樣的動蕩不安?百無聊賴的日子輾轉過去,有時顧惠懿則會望着窗前的枯枝出神,自從那天見過皇後,她就明白很多東西被一張張鐵網禁锢得嚴絲合縫,而她即便已是賢妃,卻始終得不到任何答案。
轉眼間,風過凜骨,寒陽當空,萬物陷入死寂,只不過是未有雪落,相反地,這幾日不知何故,一洗往常幹燥的氣候,每次風過,連鼻息間都可以輕易的嗅到水汽的濕潤,這種不同于以往的冷似乎可以直接侵略到骨髓裏,也因此,連顧惠懿的耳朵裏能聽到有宮女太監的叫苦不疊,其實莫說是他們,便是駐守在宮城外的禦林軍都對反常的天氣表現出極度不适應,是以,有蹊跷的言論說,此等異象與皇帝在永寧寺遇害一事脫不了關系。
不久後,皇後得知有此言論,一改以往敦厚形象,将有關者統統發配去暴室,以儆效尤,而為了整頓後宮不良之風,皇後甚至将服侍了自己好幾年的丫鬟也不留情面,不得不說,皇後的手腕真的将有關言論被壓制下去,無人在敢提及。
本以為此間種種告一段落,不想氣候反常不過三日,慈寧宮便接着傳來不好的消息,而追其罪魁禍首,便是太後沒好全的身子骨不小心被冷風激着一下,病情愈重,前朝動蕩,皇帝未歸,此種關頭,各宮嫔妃聞訊各懷心事,紛紛盤算起自己心中的那點小九九,不過大都只盼自己不要被殃及池魚,至于太後能否能挺過這一劫難,與他們也沒有任何關系。
那一天的氣氛慘淡到極致,而對于顧惠懿來說,她曾親眼見證了吉嫔的離去,又親手解決了帝姬的生命,即便太後此刻真的撒手人寰了,她心中也溢不出一點恐懼,從接踵而至的太醫,包括最後她站在太後床畔看着要油盡燈枯的‘老人’她也在好奇,為何自己所念所想,竟然都是淑妃會被黎安如何處決?
好在,最終常業不負神醫之名,與向文幾位太醫院的元老聯合施針,将太後的病情暫時穩住了。
病情一穩住,常業等人不敢多做耽擱,待太後沉珂睡去時,即刻又幾位太醫聯合商議出了一個藥方,此情此景,皇後的神情才不在緊繃,繼而緩緩舒了口氣,顧惠懿冷眼旁觀,但看着皇後真真切切為太後的病情有所牽動時,她的思緒也不禁追溯到那次黎安大動肝火,趙良的反應。
本以為太後的病情暫告一段落,不想第二日一大早,欽天監的人便高呼要求見皇後娘娘,他們口口聲聲聲稱自己有重大發現,事關國家命脈。
後宮不得幹政,不論是誰,但凡處于深宮,必将此話銘記于心,不敢違背。
也相傳,早先誠祖帝有一位才冠一時的梁夫人,但那時,祖帝就坐擁有很多傾國傾城的美人,梁夫人不過其中一個,只是祖帝對待梁夫人與其他女子不同的便是,他不僅肯為梁夫人生産時備有椒房,每日下朝時,也肯将朝政上的心結講述給她聽,開始時,梁夫人的确持有保留的态度,祖帝講過,她也不過一笑置之,并不敢多舌,等到時間一長,梁夫人便徹底淪陷在這種平靜而又‘專寵’的假象,不負才女之名,她以女性提出的建議也着實為祖帝分了不少憂。
只可惜,時間一長,祖帝的狹隘與猜忌日益擴大,這種心理落差導致梁夫人最後的結局,卻是凄涼的老死在冷宮中,無人問津。
他們的故事也許被後世添油加醋了不少,可對顧惠懿來說,卻是警告,不僅是因為她們有着同屬寵妃的共同點,也基于顧惠懿的父親是當朝的一品将軍,更為皇帝忌憚,因此,當消息一傳來,顧惠懿很好奇,這位德才兼備的皇後娘娘會做出什麽選擇?
可惜,這種疑惑沒持續多久,取而代之的便是令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
黎安回宮了!
而除此之外,回宮的這一路上,淑妃都是被當成犯人押運回來的。
“淑妃陳涵婧,得沐天恩,榮于四妃之首,然不知感念,私結草寇,為私欲置多條人命于不顧,後大逆不道,行刺于朕,經刑部、宗人府查證,情況屬實,現已定論,此舉乃萬死不足以謝罪,但念其終知己罪,苦海回頭,朕心甚痛,雖罪大惡極無赦,朕仍不忍重刑加諸,故賜毒酒一杯,保全全屍,死後革去尊榮,不得葬入帝王陵。”
這一道聖谕在三天前頒布,聖旨闡明,當初黎安在永寧寺遇害乃是淑妃一手造成,雖原因不詳,但這聖旨的最後是說,千鈞一發之時,淑妃良心悔過,硬是替黎安挨了這一刀,這才使得皇帝安然無恙。可不論這回朝廷的輿論怎樣引向,太師的人脈如何神通廣大,任誰看來,刺殺這等皇帝的大罪便是使得淑妃株連九族都不為過,退一步想,如果這道聖旨昭告于天下,那世人也只會誇皇帝念與淑妃情深,是個情深意重的帝王。
不管過程如何,以庶人之身死去,就是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最後下場。
其實顧惠懿很想問問她為什麽?為什麽肯大費周折,兵行險招,最終卻落得個自取滅亡的下場?難道只是因為此計若成,她的恩寵和地位就要陵越于所有人之上了麽?
顧惠懿無從解答,疑惑,卻又重了一分。
————
自從永寧寺一事告一段落後,黎安心心念着朝堂之事,不停歇的趕了一天一夜的路,本來舟車勞頓的他應該歇息一個晚上再做處決,不想當夜,他又在南書房召見了自稱有十萬火急要事的欽天監監正李唐。
李唐其人頗為剛愎自用,然而他對觀星象之術的天賦高超,的确頗有其才,因此黎安愛惜他的才華,使他不到三十歲官居監正一職,對他的器重也可見一般,除李唐之外,另一個低首跟在他後面的男子黎安在熟悉不過,想當初‘天象異變,災害不斷,是‘災星’降世之兆’的這句話正是從他口中說出。
黎安想起舊事,不由神情一黯,轉眸又直視着一語不發的李唐:“說罷,到底有什麽事令你不惜驚擾皇後也要上報?”
李唐上前一步,神情鄭重:“皇上,不知您是否了解北鬥七宮的七元解厄星君。”
黎安眸中帶有異色,但還是緩緩道:“是指對應天樞,天璇等宮位的破軍、貪狼、七個星子,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标,合而為鬥,世稱北鬥七星,它們不僅發生移位,鬥柄也随不同時節而指向不同的方位,這七星昭示常帶有神谕,因此古往今來,也都是你們欽天監該費盡心思鑽研的東西,你如今逢此關頭冒死也要進谏,難道是星象所指出了什麽問題,亦或者,與朕相關?”
“皇上英明!”李唐頓首再拜:“《春秋繁露》一書中早有提及,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随之。這意思是說,災為變小,異為變大,關乎于天譴的強弱,而臣昨夜意外見到夜空正上方出現了多時不見的北鬥七星,臣大喜之時,發現北鬥一天樞的貪狼星位出現了少有星位不正的異象,自古貪狼星則為神話中金鳌的化身,而金鳌則……”
李唐說到關鍵處,言語卻停頓了,他小心的觑着黎安的神色,并未在開口多言,而黎安長眉不悅皺起,眼神如鈎直盯着他,口中也淩厲道:“說下去!”
李唐複雜的道了一聲“是”又接着道:“皇上,金鳌自古代表權利和財富的象征,且不處于紫薇宮正位,如此蹊跷,只怕臣子不軌,欲行興兵之罪。”
黎安臉色越發不豫,李唐也再不敢多言,倒是身後一直膽戰心驚跟着的男子呼吸聲粗重,顯得本該空曠的南書房聲音格外紛雜,本來李唐以為黎安會發雷霆之火,卻不想黎安再度開口,卻是對準了一向膽小的季言:“若說李唐進谏為的是重中之重的國事,你來,又是為何?難不成像上次一樣,又有了什麽‘災星降世’的天象麽!”
季言年邁,膽子又小,黎安此番诘問已吓得他出了冷汗,他邁着步子上前,躲避了黎安銳利噬人的目光,緩聲道:“當初為了迎合星象,晴貴嫔宮裏的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