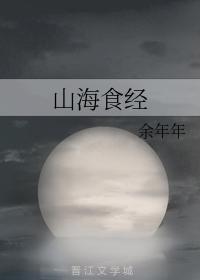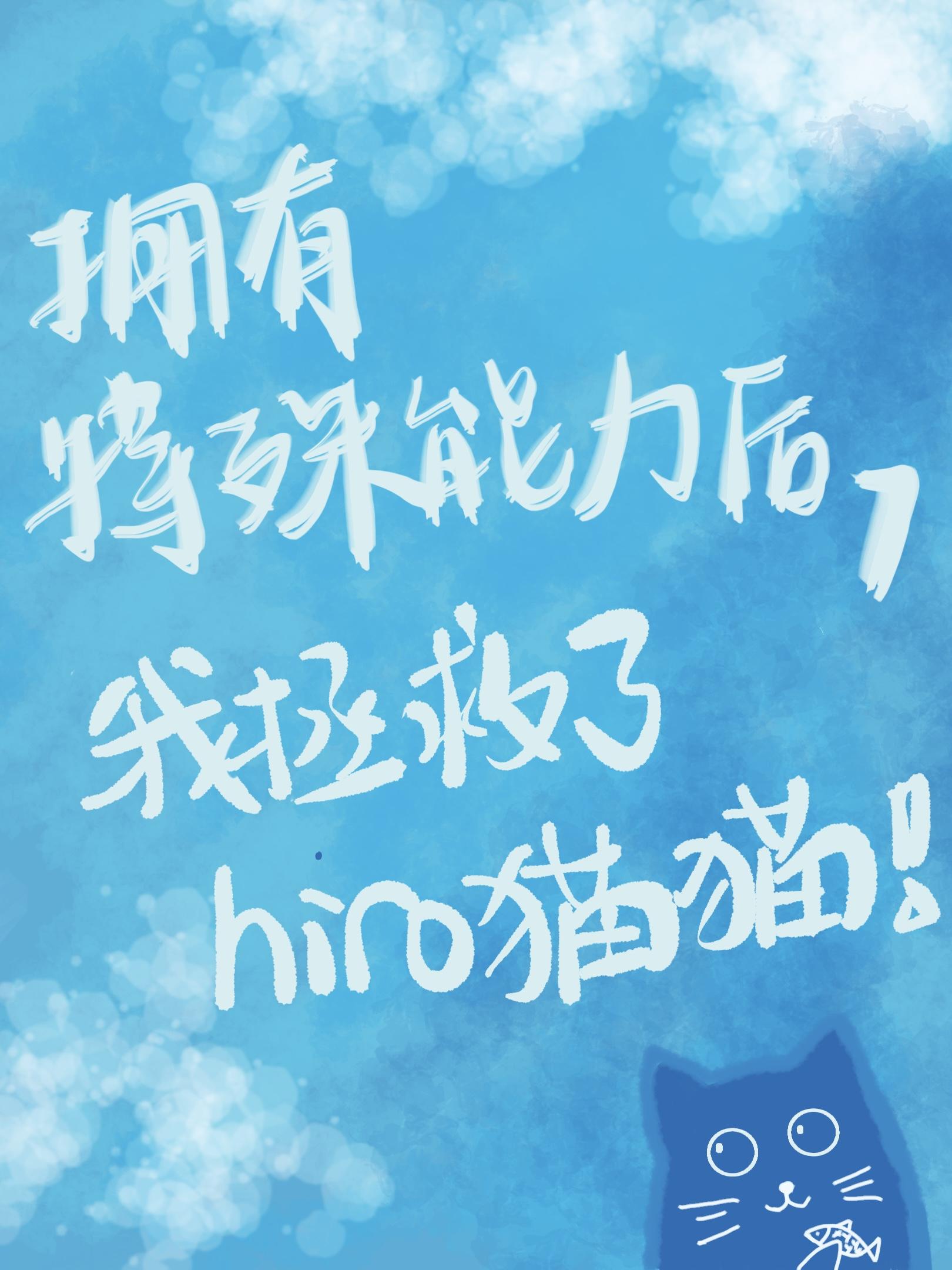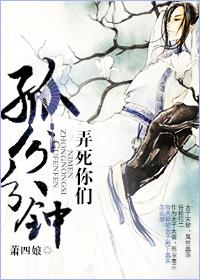? 深秋的庭院是蕭疏的,望着這一切的姬旦的神情似乎比這樣的庭院更見蕭疏。
微阖了眼睛的姬旦倚着隐幾仿佛打着盹,又似乎只是閉目靜思。深色的外袍襯得已然十分消瘦的人更添幾分嶙峋。
此時他突然開始咳嗽,似乎更加印證了這一猜想。
咳了一陣,他睜開了眼,眼睛裏絲毫沒有剛醒的茫然,清澈的瞳仁裏倒映着庭院裏的深秋景色,顯得原就淡薄的神色更添清冷。
自從歸還大政之後,閉門謝客的旦經常會花很長時間就這麽望着庭院發呆,有時候這一坐就是幾個時辰,不言不語。
仿佛有很多事情,直到卸任的當下才有空拿出來一件件梳理分明。
不是外人所想象的落寞寂寥,旦的眼神沒有這樣軟弱的情愫。倚着隐幾的他有着往日攝政時所不常見的一點慵懶,也不是全然的放松,倒像是若有所思。
眼睛裏是阗然無波,仿佛暗夜裏的峽灣,深邃平靜至不可測。
他每日還是會聽人跟他說說王上如何百僚諸王侯如何,通常不置一詞,像是聽進去又像是根本就沒聽。
種種試探都沉了底,還政後的旦甚至不如召公有與聞政事。
初掌大政的天子也在注視着這個看似平靜的庭院,讓人分不清那些谒見到底是出自那些人自己的心思還是天子的暗示。
只是這一切,旦似乎并不關心。
于是便有人說,這是真正還政于天子。一夜之間,之前所有對這位攝政的不懷好意的流言仿佛被無形地駁斥了一番。
當沉寂許久的宅院迎入了一位不速之客後,事情有了變化。
沒人料到,這個人會是唐叔虞。
旦望着坐在對面的已然身量挺拔的叔虞,有點恍惚,他忍不住咳嗽了一下,又忍住了,露出了點微帶歉意的笑容,掩着唇角的袖子卻并未落下。
叔虞恍惚覺得自己并不是幾年沒見而是幾十年沒見這位王叔了似的,那個總是讓他有高山巍巍之感的王叔何曾這樣像個病弱的老者一樣帶着虛弱同他見面過?
他幾乎懷疑是自己記岔了,又或者眼前的人不是王叔。
“怎麽想到過來呢?”
旦并沒有對自己的衰弱有任何解釋,安靜的眼眸裏仍舊是當年微帶疏離的溫和慈愛。
叔虞有些恍惚,他忍不住細細看了眼旦的神情,那清澈平靜的眼睛讓叔虞覺得方才那些關于王叔衰老了的想法實在太過無稽了。依然充滿了洞察一切的漆黑眼瞳哪裏有一點垂老的痕跡。
可細看又覺得,那些眼角眉梢的疲憊和不再如劍出鞘的坐姿,像在不小心地洩露這個男人不再是帝國核心之後的悄然變化。
時隔多年,姬旦面前的年輕人已經不是印象裏把情緒想法寫在眼底的叔虞了,他不由想起同樣已然長成的天子。
還政并不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至少在旦看起來,要比自己代天子踐祚簡單得多。
收回一切象征着天子權力的物件的誦連眼珠子裏都流淌着躍躍欲試的火焰,仿佛墨金色的瞳孔甚至讓旦有些怔忡。
那是一個天子該有的眼神,即便是代天子攝政的他都未必有過的眼神。
意識到這點的旦,神色間都帶上了更多的如釋重負。他終究是不負所托的,不是麽?
但瞥到他笑容的誦顯然不是這麽想的。
恍惚間,叔虞的聲音傳入耳際,“……王上亦十分挂念您。”
“是麽?替我向天子道謝吧。”
叔虞有些拿捏不好旦的态度。仍是當初攝政者的不置可否的反問,透着十足疏遠的道謝,無法聽出言下到底有幾分真意。
“王叔久不出門,大家也都十分關心。”
叔虞觑着旦的神色,對方卻一片漠然。
“王上對王叔始終是心腹視之的,王叔王事憂勞多年,這份功績是如何也不能抹殺的。”像是在斟酌措辭,叔虞這番話說得格外慢,仿佛是為了看旦的反應。
旦只是擡眼看着他,似乎在催促他說下去。
見他不說話,旦緩緩開口道,“王上要如何處置我?”
“這……”
叔虞一時有些結舌,他到底是低估了自家王叔,也許連他王兄都低估這位看似溫柔和善的王叔了。
這人雖是囿居一隅,卻仿佛什麽都已知曉了。那些熟悉的敬畏又逐漸浮上這個已經年紀漸長的青年人的心頭。
他甚至不需要知曉什麽,而僅僅是從叔虞的到來和他看似無意的話語便猜到了一切。
“王叔千萬不要多想,王上并未對那些谮言有何反應。”
“但也沒否認,是麽?”
叔虞睜大了眼,卻不知如何接口。盡管旦說的是真的,卻不是他可以承認的。看到默然以對的叔虞,旦的神情透着了然。
“我已然歸還大政,王上如何處理,我都在此候命,請轉告王上,不必擔心。”
望着連語調都沒有變化的旦,叔虞甚至有些後悔來這一趟。
“我倦了,若是無事,還請自便。”
沒料到自己竟會被逐客的叔虞吶吶地行了禮向外退去,之後便匆匆離開了。
旦仍坐在原處,望着連茵席都有些歪斜的原先叔虞的坐處,嘴角挂着笑意,眼神裏卻是比秋日還要深沉的冷意。
叔虞已經長大到可以在他面前玩弄這些虛虛實實的把戲了,他确實是老了,恐怕,天子也這麽覺得吧。
罷了,終究是年輕人的天下了。
如是想着的旦,望着天際沉甸甸的鉛雲,微蹙了眉,忍不住又咳了幾聲,方才近乎強硬的模樣終于漸趨瓦解。
旦的神色不無自嘲,未料到老了,尚有此等颠簸,若是卒于異鄉,還能不能歸葬王土呢。
這個問題直到他和幾個仆人消失在王城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時,他也未能得出一個答案。
自洛邑至楚地,連旦自己都快忘了已經出發了多久。
與京師裏所傳言的狼狽逃亡稍有不同的是,這個儀容絲毫不亂的男人連一絲可稱之為惶恐不安的神情都不曾有,秀長的眉眼貯滿了深沉淡然。
京師的流言如雨夜春草潛滋暗長,他的閉門不出只是讓這些言辭愈加嚣張,流動在沉默的天子與前攝政之間的空氣變得越發凝滞。
姬旦并沒有在這樣令人不安的氣氛有分毫的舉止失措。
他忍不住想,若是再也不回到洛邑,不回到鎬京,會不會也是個不錯的結局呢。
他并沒有認真地想下去,在他散亂的思緒逐漸飄遠時,這一天,他終于到達了目的地,等待着他的正是當日為文王師的鬻熊的後人。
荊山之下,這群服色迥異的人卻帶着十分溫厚的笑容,将這位不知何故離開周都來到此處的尊貴的客人迎入了他們的住所。
相比随行而來的人,旦卻像是十分熟稔的樣子,溫聲與帶頭的男子交談着,這人正是鬻熊的孫子熊狂*。
熊狂十分瘦削,身材也不高壯,深色的皮膚昭示着這位領頭人稱不上安逸的生活。
被迎入室內的旦行過客禮便施施然落了座,他自幼跟随父王兄長左右,對這先祖曾帥民投附的家族不能說不了解,甚至并不僅僅是了解。
難得顯得有些熱絡的旦,竟開始絮叨起了陳年往事。
鬻熊出自祝融八姓之一,曾為文王火師,旦不由想起許多年前的牧野一役,垂下了眼簾,唇邊的笑意又加深了少許。
楚語不同于周人語言,随從而來的人幾乎是有些尴尬地侍坐在下首,而與熊狂順暢交流的旦在他們眼中也顯得越發神秘莫測起來。
楚地尚巫尚赤,或許是受這花紋詭麗的紅色袍服的影響,绛色博袍的頭領顯得分外熱情。
一身玄衣的旦愈發有些嚴肅端莊的樣子,在聽到對方詢問來訪目的時,卻沉默了一會兒,有些含糊地說道,“旦自冗務中掙紮而出,便來會會故人而已。”
接着又将話題轉往當日鬻熊如何助文王伐商,熊麗又如何舉族遷徙至于此地,說罷又是一陣唏噓。
熊狂不再多問,只說設宴款待。
當晚,賓主盡歡。
旦自來淺眠,這一日又飲多了酒,休憩不久便披衣起來,只管對月閑坐。卻不料有此雅興的非他一人,只見踏月而來的卻是熊狂。
“可是飲得多了?”
“年齒漸長,耐不得如此豪飲了。”旦笑得有些無奈,仿佛真的在感嘆歲月不饒人,又好似只是随口說說。
“您年歲并不大,何必早早當個閑人呢?”
轉頭看着随意坐下的熊狂,旦的眼神有一瞬的精光閃過,卻又轉過眼只是望着朗月淡淡道,“旦受托于先王,輔佐王上。昔日王上幼弱,不得已代其踐祚,如今王上長成,自然要奉還大政,北面事之。”
“善始善終,君當無憾。”
旦沒有回答,只是笑容淺了一些。
“未必無憾,倒也無悔。”許久,他如是答道。
熊狂的神色似是有些動容。
眼前的人自然是君子,但一個攝政七年雷厲風行的人,定然不會是像他所說的這般簡單平易。
“如今是用人之際,祖上既有如此勳績,豈能囿于此地?”
“君有此言,吾當孰計之。”
熊狂的爽快倒是有些出旦的意料,只是這份驚訝卻被遮掩了過去,夜色下,他仍是平和溫良的面孔。
時已入秋,夜風寒涼,即便是比豐鎬二京要靠南,楚地的夜也依舊是冷的。
熊狂離去後,旦仍靜坐了許久。
比起旦的悠然,此刻擰着眉頭的成王顯得要焦躁許多。
召公與太公自來是八風不動的樣子,襯得剛加元服的年輕天子好似又回到了之前的少年樣子,惴惴不安寫在臉上。
“王上,旦此去應是前往楚地。”
“王上,四境安定,您不須如此。”畢竟是自己外祖,太公開口,成王終于不再背着手來回地走着,而是端正地坐下。
“這樣大的事情,竟在人都快走了三天才報上來,如今又說不曾追上,難道要孤親自駕車去追嗎?”
“王上,慎言。”
太公的眉頭蹙了起來。雖然是幼沖登位,親政日淺,然而這樣失了分寸的天子也是少見的。
“王上,旦絕非行事莽撞之人,其中必有隐衷。”盡管是衆人心知肚明的緣由,召公姬奭淡淡說來卻終于将天子的怒火澆熄了。
這個暗潮湧動流言四起的京師,在場三人都心如明鏡,尤其是年輕的周天子。
天子并不敢再說什麽,他的太保盡管從來沒有對他發過怒,平日有行止不當之處也是耐心道來,處理宗族事務一向深孚衆望,頗是得了些好脾氣的名聲。
但他是記得的,當日王叔姬旦決意代天子踐祚時,這位傳聞中最是好說話的召公姬奭與太公是怎樣逼得這位先王最看重的弟弟,當今天子的親叔叔指天誓日剖白心跡的。
想到王叔姬旦,誦的內心又是冷一陣熱一陣,辨不清個滋味。
太公咳了咳,仍是不動如山的樣子。姬奭振開衣袖施了一禮道,“當日管蔡流言動搖國祚,有賴太傅東征得以平息,如今流言再起,旦遠避楚地乃無奈之舉。大周立國日短,實不應讓社稷之臣寒心。”
話裏隐隐的譴責之意讓誦又是惱怒又是不安。
他畢竟年輕,那些賢人諸侯看他的目光哪怕多了一分審視也足夠令他坐立不安,好像坐在桌案之後的人不該是這個年輕人,而該是他年紀也并算不上太大的王叔。
他忍不住想,如果是王叔坐在此處,這些人還會用這樣的眼神打量麽?還會用這樣不着痕跡的怠慢的語氣說話麽?
諸如此類的念頭一旦泛濫便讓他寝食難安,也就越發容易行差踏錯。
他終究不是笨人,不會直眉楞眼地與早已不問政事的王叔過不去,但每一個朝見天子的人似乎都要分去幾許目光給王城另一處的前任攝政。
洛邑王城中除了王宮路寝,亦有這位前任攝政的住處,雖與太保一樣的形制,誦總疑心諸侯朝見時,人們總會将那處認作明堂。
他不會将這些近乎荒唐的念頭傾吐給任何人,哪怕是叔虞。他能做的,便是極少去洛邑接受諸侯朝見而已。
不論如何掩飾,年輕天子的操之過急還是被太公與召公看在了眼裏。他們固然料到姬旦不會繼續默不作聲,卻不曾想到他竟決然奔楚。
一向回護天子的王叔,竟将天子置于如此境地,是二人始料未及的。
但對此感到更加始料未及的年輕天子讓兩人意識到,叔侄倆的嫌隙又并不似他們所擔憂的那樣。
不安的天子逐漸鎮靜下來,将姬奭的話細想一番,這才有些赧然。
身為天子,他舉措失當在前,行止失措在後,也難怪受到身為太保的姬奭的責問。
姬奭在宗族長老中的地位幾乎是超然的,這點哪怕是手握大權時的姬旦也未必能及,當日兩人聯手,內弭父兄,外撫諸侯,這才将将穩定了這個由于武王驟然崩逝而風雨飄搖起來的新生王朝。
連居住岐下的宗族長輩都分外客氣相對的召公奭此刻望着天子的神情并不算嚴厲,然而天子心下一凜,殘餘的焦躁也終于消失無蹤。
召公望了望漸陰的天色,緩緩道,“或者旦留了只字片語也未可知,讓府中的人留意一番,若過兩日仍無任何消息傳來,王上再遣使赴楚為時不晚。”
掩在衣袂下的雙手緩緩握緊,誦的聲音有些低沉,“便如此吧。”
姬奭望了望垂眸不語的天子,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側過身行了禮便要告退。誦一擡頭,發現自己的外祖與太保已退至遠處,正靜靜地望着自己,這才略顯心不在焉地致禮。
姬奭走了兩步忍不住低聲道,“若讓旦看見,會覺得失望吧。”
創立禮樂制度的周公姬旦不僅如是要求自己,更是不能容忍天子有任何不符合禮法的行為。
所有的禮都離不開一個敬字,敬天敬祖敬生民,只有莊重的敬意才能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法。
焦躁不安的天子在無意識的輕慢裏,已失去了對禮法的敬畏。
但那正是周王室立身立國的根本。
身為天子身側的元老重臣,時刻處在風口浪尖的姬旦已經竭盡全力,年事已高的太公也鮮少幹涉王事,許多重擔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姬奭的肩上。
姬奭一向為人寬忍,卻心思極密,他望了眼仍舊精神矍铄的太公望,淺施一禮,“可要同去旦的府上?”
對方滿布皺紋的臉上似乎帶了點笑意,接着點了點頭。
他們徑自往姬旦的住處而去,步速并不快,許是為了遷就太公的年紀。不出姬奭所料,方才還與二人交談的天子竟已然出現在了這裏。
望見二人進門的天子仿佛有些尴尬,卻仍是平靜地與二人見禮,像是自己的出現并無任何不妥,而二人相攜而來的意圖他也心知肚明似的。
正當誦想着該如何開口時,先前被天子支使着四處翻找的內豎伏身跪在門外,說是尋得了一個匣子。
屋內的三人也不明白這匣子有何不同,便讓人呈上來看看。
姬奭一望見匣子便轉頭望了太公一眼,兩人便對這匣子裏的東西心裏有了數。
天子皺着眉,這匣子的式樣讓他覺得熟悉。匣子上的鎖鑰已被打開,打開匣子,只見裏面卻是一份策簡。
這樣的冊書并不常見,姬奭仍記得當日那個藏在金縢中的簡冊便是這個樣子。*
不出召公所料,這正是一份禱書,姬誦盯着短短的幾行字,一時竟讓人看不出天子的喜怒來。
姬奭微感不安,示意旁人都退開并将門掩好,這才重新望着怔忡不已的天子。
姬誦看了許久,才将策簡放在一旁。掩上門的室內有些昏暗,帷幕一側點起了燭火,映着周天子年輕的臉龐卻愈顯蒼白陰郁。
若不是姬奭正望着天子,光影交錯間,他幾乎不曾注意到天子置于膝上的手背沾染了一滴圓形的水漬。
不待召公再問什麽,姬誦忽然站了起來,聲音仿佛有點鼻音,“請您盡快派人将王叔接回來吧。”
說罷便急匆匆地離開了,盡管并未失儀,仍是稍顯失态了。
還不能很好掩藏自己的情緒的周天子,離去得幾乎狼狽。
姬奭拿起讓天子變色的禱書,上面不過短短幾行字,卻讓他明白了天子失态的原因。他想着那時天子尚且年幼,驟然擔着邦國重任的姬旦立于清晨寒冷的江畔,仿佛沒有意識到滲着血絲的手指的疼痛,像他當日如何焦急地懇請先王允許他以身為質一樣誠懇地祈求神明将降予少年天子的懲罰都施加給他,清晰地如在眼前。
這個在告誡伯禽時頗以自己“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為重的人,在面對周天子不可逆料的病情時,便将自己的千金之軀視若等閑,好像随時可将自己的性命與神明先祖做交換。
一旁同樣看完禱書的太公嘆息一聲,便離開了。姬奭望着裝禱書的匣子,神色沉靜,仿佛在深思,漆盒上繁複的花紋在提醒他匣中之物該如何的不同尋常,而他似乎在端詳這個匣子又好像什麽都沒看。
跳躍的燭火映着古井深潭一樣的眼眸,讓人看不出這位天子的太保在想些什麽。
姬奭很快便按天子的吩咐準備派人前往楚國,只是還未等到人走出多遠,便有人來報周天子,姬旦的車駕已然在返回途中了。
天子聽到後只愣了愣,便吩咐要親自郊迎。
一旁立着的芮伯*忽然開口道,“與太傅同歸的尚有楚人世子熊繹。”說完便斂着神色,眉目無波地站回原處,似乎只是無關痛癢地提醒了天子一句罷了。
此時正是秋觐,之前天子所接見的諸侯比起其父當日又要多出許多——許多宗室子弟在殷商故地上建立封國,也是姬誦第一次以天子身份完成觐禮。
他不知自己的王叔與長輩們是否滿意,尤以姬旦的沉默最讓他不安。盡管在這之前,他的王叔對他也從未有過責難。
但那些諸侯國于他是叔伯舅父*,是藩屏周室的功臣,而楚人卻是并無任何爵位在身的,連這個世子稱謂恐怕也讓芮伯躊躇許久。
姬誦蹙着眉,遲疑地望了眼召公,姬奭垂着眼,不知在想什麽。倒是一旁的畢公開了口,“昔日鬻熊為文王*火師,熊狂亦襄助伐纣,王上不宜怠慢。”
至于熊盈諸族随徐戎淮夷參與反叛便又略去不提了。
天子沉默着,雙手在膝上松了又緊才道,“寡人昔日亦曾聽先王與王叔提及此事,既有功于周邦,雖是世子,諸卿來日也須随寡人以禮相迎。”
衆人頓首稱是。
這個當日克殷時并不曾被重視的蕞爾小邦,何以派了他們的世子随着天子太傅觐見天子呢?
也許不是所有人的都不明白,只是明白的人并不會開口。
轉眼便等來了姬旦的車駕,卻不料在郭外*,姬旦便與熊繹分開,車駕并不能從臯門*長驅直入直到應門,但有了太傅的吩咐倒也迅速地将熊繹領到久候的天子與諸卿士大夫面前。
穿着迥異于諸人服色的年輕人并未有失禮之處,不知為何,天子的神色似是有些失望。
姬奭望了一眼天子,便轉身對這位年輕人表達了周王室的關切之情。天子沉靜地端坐着,也不知是否有聽到太保與熊繹的對話。
正在此時,內豎們前來禀報,姬旦在外等候。
這個他再也無法徑直入內的明堂在他北面稱臣之後已經鮮少迎來他的身影了。被召入明堂的姬旦也并未如以往一般與召公一左一右夾弼天子,而是在熊繹一側端嚴地跽坐。
像是帶進了一陣風似的,幾乎人人都下意識挺直了上身,等着姬旦說話。
而姬旦卻只是望着天子,神色平和,仿佛自己這個不速之客也不過是來聽天子有什麽勸慰的話罷了。
姬旦略顯反常的行徑使得不僅是天子,甚至召公畢公等人也不由略帶猶疑地望向他。
此時正該是天子賞賜熊繹的時候,姬奭适時的把問題遞給了姬旦,許是為了緩解場面的僵硬。
“王上已立政,此事由王上決斷即可。”
天子的冕旒似乎晃動了一下,只是挺拔的身形又讓人覺得只是錯覺。姬誦的聲音很是和緩,面向熊繹道,“茲念爾祖考大功于邦國,賜位子爵,封地五十裏于楚蠻,世居丹陽。”
一旁等候班賜冊命的官吏已步下階阼,除了爵位封地自然還有與之相配的輿服賞賜,熊繹的神情既沒有過分的欣喜也沒有外露的失落,只是平靜地感謝了周天子的冊封。
天子銳利的視線穿過冕旒牢牢地釘在熊繹一旁的人身上,被看着的人卻似乎無知無覺,好像一點也沒興趣知道天子為何不冊封熊繹的父親熊狂,而選擇了一個甚至比天子還年輕些的少年熊繹。
微薄的賞賜仍昭示着這個新生的子爵國在周王室封建的諸侯裏是如何的無足輕重,熊繹甚至能想到哪怕多年後,自己的子孫承緒爵位,将這五十裏的不毛之地變成沃野千裏,也未必能得到周天子幾分高看。
但這至少是個不錯的開始。
念及此,熊繹看向身邊這位與父親交談許久的周室執政,眼神裏是難得一見的溫和。
感到身邊之人無聲的謝意,姬旦的神情并沒有太大變化,他知道,上首的天子還在死死盯着自己。
只見他伸手輕拍了下熊繹的臂膀,似乎是示意自己的領情,接着又頂着天子頗帶壓力的眼神說了一兩句勸勉的話。
就在衆人以為可以開始進行準備許久的燕禮時,姬旦忽然開口了,“王上,臣年事已高,懇請允臣歸老封邑。”
原本有低低交談之聲的明堂霎時一片寂靜,一幹執政齊齊看了過來。
“臣甚是思念豐地故老舊交,望王上準許。”
“王叔……”
幾不可聞的聲音自天子口中逸出,姬誦動了動嘴唇,卻不知該說些什麽。他無論如何也不曾料到這個自他幼時便一直輔佐在側的人有一天會想要離開,方才着意想探知對方對自己稍顯薄待的賞賜的看法的心情一時煙消雲散,像是三九寒冬飲了冰水一般。
天子沉默,旁人又實在沒資格開口,才要活泛起來的場面又僵住了。
召公一振袍袖,拱了拱手道,“王上不若讓衆人先預備燕禮?”
天子像是終于找回了神魂似的,忙不疊地點了頭。待轉移到另一廳堂等候的天子面對眼前僅剩的幾位重臣時,終于忍不住拔高了聲音問道,“王叔為何要走?”
他想問的當然不止這一句,但最想問的卻正是這句,從姬旦猝然奔楚開始便一直想問的一句。
“王上,臣已老了,該讓賢了。”姬旦的神情很是淡漠,似是說着再普通不過的一件事。
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姬旦攝政七年卻已覺得耗光心力,這個剛剛安定下來的王朝浸透了他全部心血。他從沒忘記父親與兄長對這個天下的期待與遺憾。
于天下,于父兄,于自己,他已算盡心盡力,如今,只剩功成身退了。
分封四處的諸侯可以藩屏周室,文王與武王的兄弟子嗣也在畿內履行着王之卿士的責任,他還有什麽值得戀棧不去的呢?
天子和卿事寮太史寮中的諸位大臣無論真心還是假意的挽留都未能動搖姬旦的決心。去留之際,沒人比他更明白,未來或有的太平盛世已經不需要他垂老的身影了。
卻是召公冷不丁地問道,“旦欲何人以代君職?”
姬旦沒有看向臉色丕變的天子,而是看着與他一東一西分陝而治*的召公姬奭,眼角染上一絲笑意,輕聲道,“此事亦須天子裁奪。”
伯禽已是魯侯,有望繼任周公分掌半壁天下的,不出意外,應是姬陳。*姬奭不由想起姬胡*,當日囚蔡叔于郭鄰的人面對比起他父親更加溫和唯唯的子侄,終究還是給予了卿士的地位。
這天下必要在姬姓手裏才能安然,也只能在他們手裏。
天子顯然并不願意馬上答複,畢公則提醒燕禮将要進行,似乎沒有多餘的時間留給天子提出更多質疑,一行人便又前往路寝*。
姬旦在觥籌交錯間仍是那個處處妥帖從無逾矩的前任攝政。天子行一獻之禮後便是主賓間的酬酢,姬旦嗅着空氣中熟悉的郁鬯的香氣,望着宰夫以主人禮飲于國君衆大夫有些失神。
當日武王克商大會諸侯,代主人禮的正是當日為冢宰的姬旦。
燕禮本就是為了飲酒,至無算爵衆人已然有些酩酊之意卻也不敢失禮,脫屦升座以盡歡的天子路寝中,來自蠻荊的少年仍是清醒的很。
天色漸暗,漫長的燕禮尚未結束,天子的阼階上已有手執燭火的庶子,燭火映着天子略顯沉郁的面色無聲跳動。四散庭中執燭的甸人與庭外的阍人則像是沒有注意到兩位執政離席的身影。
夜風卷起玄端的下擺,兩人立在陰影處,姬奭忽然一嘆,“你比我年少些,這白發卻多我許多。”
姬旦下意識撫了撫鬓角,淡淡道,“畢竟是老了,不敢與兄長相比。”
姬奭搖了搖頭,“你一向比誰都明白,王上卻不明白。”
姬旦笑了笑,他從未打算瞞過這個明察秋毫的庶兄,“天子終究會明白的,他會的。”像是為了說服自己似的。
姬奭忽然不想問了,為什麽選在這個時候奔楚,為什麽帶回熊繹,為什麽那冊禱書這麽湊巧地被發現,為什麽在天子滿懷愧疚的時候決然離開。
他一向懂這個弟弟,但也時常不是那麽明白。
就像當日面對武王薨逝後混亂的朝局,當日面對武王傳位稽首而泣的人卻沒有遲疑地代天子踐祚,置自己于炭火之上。
人的心或者大的能算計天下,有時候卻又小的顧不上自身。
“不知何日再與君對弈同飲了。”姬奭負手望着遠處,有些嘆息。
“技陋之人唯掃室以待。”說罷,姬旦長施一禮。
宴會快要結束了,姬奭嘆了口氣,“我不如君,甚矣。”說罷便離開了。
《陔》樂的聲音消散在夜風裏,天子卻又高坐在阼階上,看到姬旦走來,年輕的天子低低地喚了聲王叔,希望他能像從前一樣走上阼階,安撫有些醉酒的自己。
然而姬旦卻止步于阼階,恭謹而沉默地跪坐着,眼神仍是溫和的。醉了酒的天子只覺得怎麽看,這個肯為自己擔下天譴的叔父都冰冷而遙遠,夜色裏連神情都是模糊的。
憤怒而傷心的天子卻沒有發作的跡象,他不能。
姬旦俯身再拜,姬誦明白這是辭行的意思,不是天子送賢者離去的辭別,只是家中操勞已久的叔父來向自己侄兒告別。
“王上善自珍重。”
“王叔……”
姬旦離去的身影頓了頓,卻終究沒有回過頭。
當日勸谏君王的《無逸》還攤在案幾上,他的王叔卻再也不會這樣殷殷叮囑他了。廣闊的路寝裏,內豎都被遣退了,沒人會看到阼階上天子微微抖動的雙肩和冕服上不斷擴大的水痕……
庭外,月色如洗,修長的身影伫立了一夜。
*熊狂:關于此時熊狂是否在世存疑,為了行文方便,如此設定。熊繹的年齡則大體根據史料,然而三代資料混亂,姑且存疑。又及鬻熊史載活至成王,有求教康叔封于衛之事,大概活了一百二十歲,竊以為未必為真。
*此處按《今古文尚書注疏》中《金縢》的有關注釋,即“秋未獲,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非周公卒後而是周公居東之後,即不采《史記》所說。注疏疑秋未獲之前有脫簡,未知哪年之秋,而《史記索隐》據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當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誤。且校于《今本竹書紀年》,私以為開《金縢》為武王卒後流言四起之時。而此處或是後文成王所作《薄姑》(今佚)之逸文。是以此時召公已知金縢所藏為禱書。
*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載:“武王時,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有關論文推測芮伯負責諸侯入朝觐的相關事宜,此處便依此虛構。
*《儀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何尊銘文: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敬享哉!’蓋稱文王,武王應無不妥。
*按楊寬先生所說,成周城應為小城連大郭的形式,則周公如從南來,或止于洛河南岸(即外郭應跨洛河南北)。
*臯門,應門: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五門
*唐蘭先生以為應作分郏而治,郏即郏鄏,即洛邑為天下中心,而周公治東國,并且以《君陳》中命其分正東郊成周為據,此處存疑,仍用分陝而